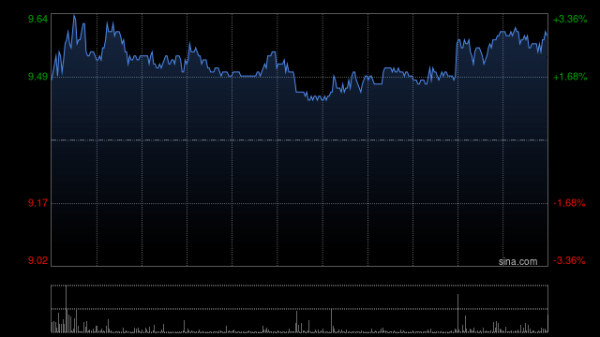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求股票配资,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。

嘉庆八年,闰二月。
风寒料峭,真正意义上的春天,还远远没有来到。
地点,是贵州仁怀。
仁怀有个叫做石缸湾的地方,这是个村子,村里住着一个叫做邓铎的村民。
邓家,祖祖辈辈都是庄稼汉,邓铎也是务农为生。
邓家的后边呢,有块地,这块地什么都好,就是不好浇水,因为这块地啊,它和河流不在一个坡度,所以要靠木杌来引水。
什么叫做木杌呢?就是先砍伐一棵合适的树木,一般是比较耐水耐侵蚀的松木或者杉木,然后把树干剖开,凿空,做出一个槽来,这就叫做木杌。
把这个木杌一头搭在河流处,另外一头搭在地里,这么一来,高坡度的水就能灌溉到低坡度的田地里。
前两年,邓铎制作了一个简单的木杌,勉强还能用,可是今年这眼看就要开春了,木杌却被虫子给蛀了,坏掉了,不能用了。
别人家都灌溉引水,自己这块地却灌溉不上,邓铎这叫一个着急啊,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,直接从河流这一块,挖一条小沟,把这个沟啊,挖到自己的地里来,这么一来,自己的地就吃上水了,等吃水吃饱了,自己再把这沟给填平了,这期间自己还能再做一个新的木杌出来,岂不是两全其美?
理论上邓铎的这个办法,是可行的,唯一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,邓铎这块地和河流的中间,盖着一座孤坟,是村里陈老太太的坟冢。
但是邓铎也想到了,自己要种地,要取水,可也不能打扰先人,所以他打算要挖的这条沟啊,都是绕着陈老太的坟冢挖的,而且离的也比较远了,在史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“暂欲开沟引灌,相离伊坟甚远”的记载。
计划好了,邓铎就打算开挖了,但是这第一锹还没下去,陈老太的两个儿子,一个叫邓钱,一个叫做邓钦立刻跳出来阻拦,说你挖一个试试,你看我们哥俩弄不弄你。
地,是国家的,是公家的,谁搞破坏都不行,但是邓铎只不过是挖一条小小的沟渠引水,其实这是很合理的。

但是,邓家兄弟认为不合理,两个兄弟就觉得,既然我母亲的坟冢就在这里,你邓铎动土,就说是离得远,你也就远个几百米,这几百米能管什么用?
一来这是我两兄弟母亲的坟,你在坟前动土,你就是不敬,二来古人都迷信风水之说,先人陵寝的选址和保护,都和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,邓家兄弟认为,邓铎如果要挖沟,就是在破坏母亲的坟脉,坟脉一旦被破坏,子孙后代都要遭殃。
所以,两兄弟是说什么都不让挖。
邓铎在田里等水,这水就是救命的水,有了水,庄稼种上了,有收成了,一家人才能吃上饭,庄稼种不上,一家人就得饿肚子,饿肚子还是好的,饿死都有可能。
可是,邓氏兄弟和两个门神一样,堵在路上就是不让邓铎挖,这给邓铎急的是直跺脚,他实在是没办法,只好诉诸于官府,希望官府里的老爷们能给自己做主。
邓铎告什么呢?告邓氏兄弟阻水,阻碍自己春种秋收。
官府接了诉状,立刻就点了两个衙役,一个叫做罗起俊,一个叫做郑洪升,让二衙役拿着票,去传唤邓氏兄弟过堂回话。
二衙役没有直接到邓氏兄弟的家里,而是找到了村里的乡约汤怀畅,让汤怀畅带路,带着二人去找郑氏兄弟。
乡约,就相当于是村主任。
到了邓氏兄弟的家里,二衙役也不啰嗦,传票拿出来是哗啦啦一扬,说奉了官府里老爷的命令,传唤你们二位问话,你俩兄弟,赶紧收拾东西跟我们走吧就?
邓氏兄弟,只有邓钦在家,邓钦一听衙役这么说,他心里老大不乐意,他说屁大点事儿,就是不让邓铎挖个沟,还至于闹到官府里,我还成被告了?
所以邓钦把腰一插,说此等小事,何劳我去?我没空,我去不了。
您看邓铎姓邓,邓氏兄弟也姓邓,想来这个邓姓啊,在石缸湾是大姓,
别的不说,这个事件中的邓铎,邓钦,邓钱之间,就有亲戚关系。

可以说,石缸湾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同姓聚居村落,邓姓在这里就是绝对的主导大族。
这小小的一个村庄里,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,不是亲叔伯就是堂兄弟,关系非常复杂,盘根错节。
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理解,在邓氏兄弟看来,他们阻止邓铎挖沟,维护的不是他们两兄弟的利益,而是整个宗族的风水,这是阖族大事,官差凭什么管?衙门又凭什么过问呢?
在邓钦的眼里,二衙役既是官府的人,那就是外面的人,他们进村办案,是人生地不熟,两眼一摸黑,他们在这片根本就吃不开,如果吃得开,怎么还得靠乡约带路?
所以,邓钦是压根不害怕。
可是我们想一下,衙役是带着官府的老爷签了字的传票来的,那这就具有法律效力,到你家中来,让你去回话,你不去,这可就是公然抗命。
族规,难道还能大于王法吗?
衙役郑洪升把眼睛一瞪,心说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,立刻指着邓钦的鼻子是大声训斥,说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,官府传唤你,你敢不去?我看你是欠收拾。
这邓钦呢,可能平素欺行霸市,他就惯了,不然干嘛邓铎挖个沟他也要百般刁难,衙役训斥他,他丝毫不惧,反而是拧身就走,那意思就是爱谁谁,爷可没工夫搭理你们了。
郑洪升一看邓钦要走,那指定不行啊,他眼疾手快,一个箭步冲上来,把手一伸,像老鹰捉小鸡一样,直接就把邓钦给扣住了。
郑洪升毕竟是衙役,练过两下子,单手就制的邓钦不能动弹,邓钦受制于人,十分不快,他连吼带骂,让郑洪升赶紧把他给放开,说要是伤了自己,保管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
就在这个时候,邓钦的兄弟邓钱刚好从外头回来。
邓钱干嘛去了呢,他是早上出去砍柴了,所以他回来的时候,手里正好拎着一把柴刀。
走到门口推开门,邓钱一看,兄弟邓钦竟被衙役扣在手里不能挣脱,邓钱也不管三七二十一,心里这火蹭一下就上来了,他也大声叫嚷,说赶紧把我兄弟放开,邓铎那厮是诬告,我们绝不去官府!
郑洪升一听,他是纳闷了,自己是官差啊,奉了上官均命来传唤,你俩是平头百姓,既然涉案了,那就有义务跟我们回去,去配合调查,来你家叫你俩,这完全符合工作流程,你邓氏兄弟二人,怎么就蛮横无理,死活不去呢?
所以郑洪升手没松,而是冷笑一声道:
真假虚实,谁没错谁有罪,到了公堂之上自有上官明断,你俩就给我老实点,抓紧跟我们回去。
邓钱一看郑洪升还不放手,倏的他从心里就升起一股无名怒火,他是恨从心头起,恶向两边生,他三步并两步,冲到郑洪升的面前,举起柴刀,对着郑洪升的脑袋就劈了下来。
值得注意的是,邓钱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,他虽然持刀行凶,但是他用的是刀背,等于是这一下不是劈砍,而是夯击。
可这毕竟打的是脑袋,力道也不小,这一下打的郑洪升是眼冒金星,当即松开了抓着邓钱的手,要说毕竟是衙役,练过两下子,郑洪升尽量保持身体平衡的同时,还伸手想要把邓钱的柴刀给夺下来,但是郑洪升没想到,邓钦被他抓了半天,心里憋了一肚子气,他一看兄弟都动手了,他也要凑热闹,从地下捡起一根木棍,照着郑洪升的胳膊就是一下。

郑洪升头还晕着呢,胳膊受此一击,又吃痛的厉害,但他还是强忍疼痛,一只手要去抢邓钱的柴刀,另一只手则去抢邓钦手里的木棍,要把这两个凶器给下掉,三个人因此混战一团,情急之中,拿着柴刀的邓钱为了甩脱郑洪升,又挥了一下柴刀击打郑洪升的头部,这回可不是刀背了,这回是刀刃,因此这一下击打出去,只听噗的一声闷响,郑洪升哼都没哼一声,当时就倒地不起,翻了白眼,血汩汩的往外冒,已然是昏死了过去。
您说另外一个衙役罗起俊和乡约汤怀畅就这么看着啊?
哎,就这么看着,主要您想要上前拉架,您也得敢啊,毕竟对方手里持有武器。
人总是会幻想自己很勇敢,可实际上到了关键时刻,人往往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勇敢。
罗起俊是衙役,说白了和郑洪升只是同事关系,来拿人的时候,也一直是郑洪升说话办事,罗起俊乐得清静,乡约汤怀畅,本身这件事情就跟他没关系,何况他还是村里人,哪儿有帮一个外人的道理?
而且,您看我叙述当时的这个情况用了挺长一段,实际上这都是在电光火石之间发生的,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呢,郑洪升已经躺在地上不动弹了。
事情闹到这个地步,邓氏兄弟也吓坏了,两人一看郑洪升浑身是血的躺在地上,也不知道是死是活,他们也不敢再想,兄弟二人丢下凶器,那是拔腿就跑,一溜烟就没影了。
乡约汤怀畅赶紧叫人,把郑洪升抬到村里的医馆去治伤,衙役罗起俊也赶紧返回官府,把这个事情报告给了上官。
花开两朵,咱们各表一枝。
郑洪升这伤的,可是够厉害的,在史料的勘验报告中,甚至出现了“骨损”之类的记载,说明这已经不是皮肉伤了,是内伤,而且在扭打过程中,郑洪升身上很多地方都被邓氏兄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伤,被抬回医馆之后,郎中尽力施救,可也是回天乏术,终究还是死了。
再说邓氏兄弟,杀伤人命之后,他们连夜逃窜,但是也没跑太远,到了贵州和四川交界,就被一路追捕的衙役给逮了回来。
杀人得偿命,欠债要还钱,这个案子,死的还不是普通人,而是官差,所以都不是地方衙门来处理的,而是贵州巡抚福庆亲自办。
邓钱是主犯,是导致郑洪升直接死亡的第一凶手,官司差人勾摄公事,你抗拒不从,杀死衙役,还畏罪潜逃,罪大恶极,因此被判了个斩监候,秋后处斩。

邓钦,帮凶,打伤郑洪升的胳膊,被判处杖刑四十,您知道杖击这个东西,很有讲究,要看行刑者的力道,有意饶了你,轻点打,打一百你也破不了皮,有意要整治你,重点打,卖力气,三棍五棍你就残废,至于这个邓钦是打轻了还是打重了,没有记载,不得而知。
罗起俊,汤怀畅,见死不救,很不讲究,有违道德,但也只是申斥了他们一顿,并没有再处罚。
而至于那个到官府告状的邓铎,没成想也挨了三十大板,因为官府认为,万事皆由邓铎而起,邓铎不告状,就不会有后边的一切。
官府打了他一顿还不算,从此后更不许邓铎在自家田地附近开挖沟渠,只许他用木杌取水,如果再敢挖沟,定然不饶。
一截朽木,一条未挖的沟,一把挥出的柴刀,一滩浸土的血。
往事无言,只有山风依旧,呜咽着吹过石缸湾的山梁,仿佛在问:
下一架朽坏的木杌,会在何处断裂?
下一滴滚烫的血,又将为谁而流?
参考资料:
阅微草堂笔记. 纪昀.中华书局.2014
清史大纲. 金兆丰.河南人民出版社.2016
秋审条款及其语言研究. 宋北平, 著.法律出版社.2011
辉煌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